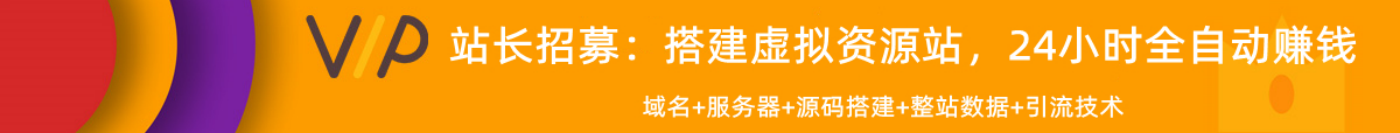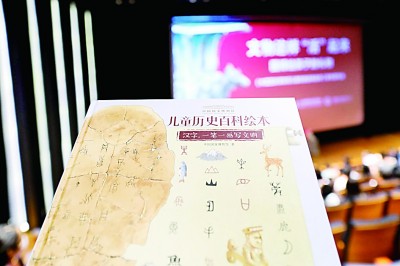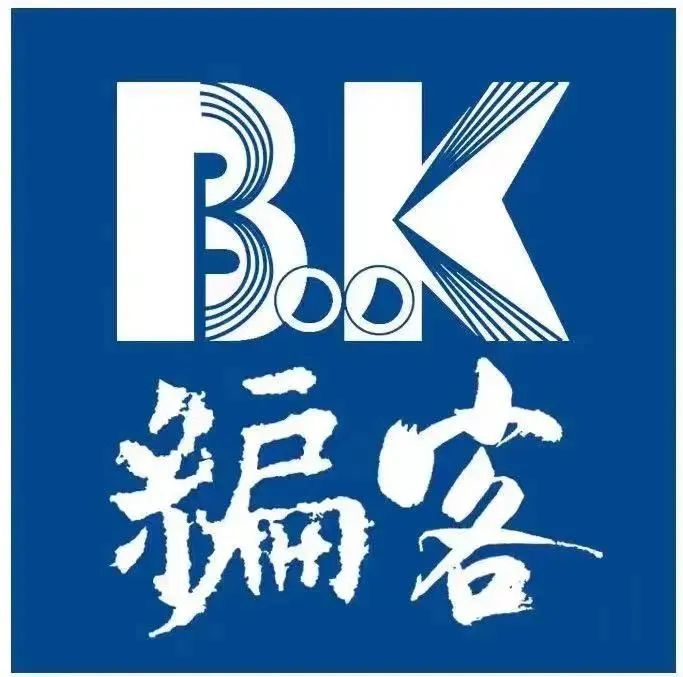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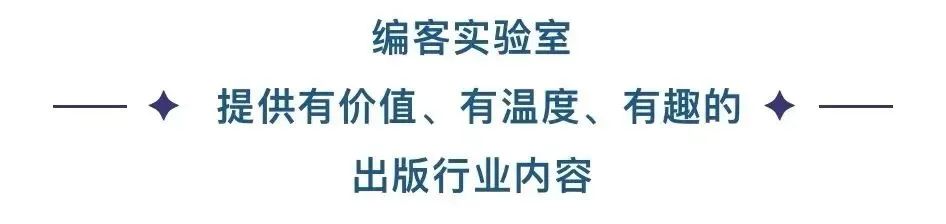
上大学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他花多年心血写的一部书稿送某出版社出版,不料编辑在审稿中,把好些本来正确的字词改成了错的,出版后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后来,我也就职出版社,进入了编辑的行列,对别人的稿件拥有几分生杀、增删、修改之“大权”。
时间久了,我渐渐发现老师当年讲的故事并未绝迹,审稿者误改原稿的事屡闻屡见。尤其令我不能释然的是,我自己也曾犯过这样的错误。每想起这些,我的眼前便不由得闪现出那位老先生无奈与激动的神态,自感惶愧汗颜,于是便想写篇东西,谈谈误改现象。抛砖引玉,若能引起同仁注意、求得方家指正,我愿足矣。
为了说明问题,先举几个误改的例子。(因材料来源多样,恕不注明出处。)
(1)毛泽东《念奴娇·昆仑》“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中)国。”(圆括号中的字词为审稿者误改的字词,下同)
(2)于谦《咏石灰》诗云:“粉骨碎身(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他别具只(慧)眼,通过稿件发现了不少文学新秀。
(4)李天佐对刘道长敬若父执(辈)。
(5)民众对陈先生遭受的不白之冤,大(打)抱不平。
(6)“他会在万籁无声时大呼,也会在金鼓喧阗(天)中沉默。”
(7)《汉书·惠帝纪》:“(惠帝)赐给丧事者,二千(2000)石钱二万(20000),六百(600)石以上万——”
以上诸例,被改之处本来无错,无烦更动,可审稿者却误以为有错,结果改出了毛病,真所谓“弄巧成拙”。下面作一些简单分析。
例(1)为毛泽东《念奴娇·昆仑》中的最末一句,原词即为“东国”,指日本。改成“中国”,与诗的本意大相径庭。
例(2)原诗“粉骨碎身”今人读来有点拗口,但合乎诗律,若改作“粉身碎骨”,于诵读是顺口了,于诗律则乖舛,于谦若地下有知,断难答应。
例(3)“只眼”一词汉语中早已有之,陆游《书志》:“读书虽复具只眼,贮酒岂如无别肠。”指独到的眼光和见解。例文中用“只眼”比“慧眼”更准确文雅,何须改动?
例(4)“父执”指父亲的朋友,杜甫《赠卫八处士》:“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改成“父辈”,意思明显有别。
例(5)大概是审稿者以为“大抱不平”是“打抱不平”的笔误,其实不然:前者中的“大”,是“很”的意思,修饰“抱不平”,整个词组指心里很是愤慨不平,只是一种情绪;后者“打抱不平”是一个成语,指帮助(受欺压者)说话或采取行动,不光有情绪,更重要的还有言行。显然,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原文表述更准确。
例(6)出自鲁迅《忽然想到》。“喧阗”是一个文言词,指声音大而杂、热闹,绝非今天我们常说的“锣鼓喧天”之误写。
例(7)是多年来出版物在数字用法方面存在的混乱状况和认识偏差的直接反映。有些同志对国家有关数字用法方面的规定作了片面理解,一看到稿件中用汉字表示的数字,往往不问青红皂白,全都改成阿拉伯数字,违背了数字用法的基本原则。本例属古籍引文,把其中“钱二万”改作“钱20000”不符合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第一条中“本标准不适用于文学书刊和重排古籍”的精神;至于将“二千石”改作“2000石”、将“六百石”改作“600石”则不但违背了上一条,而且违背了第四条中“定型的词、词组——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的规定。“二千石”“六百石”在这里是表示官职品阶的专有名词,是定型的词,不是一般的数量词组,不可改为阿拉伯数字,如同“三心二意”不可改为“3心2意”一样。
误改原作的事,不徒今天有之,古代亦不乏其例。清代大儒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就记载了不少刻书人、校书人误改原著的事例,此书卷十八云:
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壮月指八月,《尔雅·释天》:“八月为壮”。——笔者注)
现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通过数十年研究,直言:“过去从事校书工作的,特别是明代读书刻书的人,每喜凭主观判断改易古书。有时原书本不误,经过改易反致错误的却很多。”(《中国文献学》第113页,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
古今发生的这些误改原作的事例,固然令人发噱和遗憾,然发生这类失误的原因究竟何在,更值得人们深思。从上文举的例子中不难看出,误改的直接起因是“误断”:或以为对的是错的,或认为固有的是生造的,或用现在的语文规范要求古人,或毫无根据地臆测“某字为某字之误……”。因为有了误断,进而便发生了误改。
误断的发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改稿者自身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平有局限,缺乏某方面的知识;对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理解不全面、不准确;作风不严谨,不求甚解,疏于核对,师心自用;工作方法不科学,编辑加工过的稿件没有送作者审定确认。那么,如何减少、避免误改现象呢?笔者不避浅陋,略陈管见。为使条理清楚起见,不妨“开中药铺”,分五条来谈。
努力学习,不断增加知识积累
这是减少误改的“治本”之策。读书少,知识有限,脑子里只有“牡丹”“慧眼”这样一些常用的字眼,看到“壮月”“只眼”等一些稍生僻的词,不解其义,又疏于查考深究,想当然地以为原文有误,便改为自己熟悉的、似乎可以讲通的字词。只有勤读书、多学习,厚培学殖根基,疑难才会相对减少,判断是非的能力方可提高。写过《颜氏家训》的北齐文学家颜之推有句名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不免要求过苛,但读书太少,孤陋寡闻,则难免“妄下雌黄”,却一点不假。
养成勤查工具书、参考书的习惯
这是治疗误改病的可靠良方。正如《庄子》所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面前,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毕竟是有限的、渺小的,长于此而短于彼,不可能单凭脑子中已有的知识解决碰到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审读专业性较强的书稿时,更是如此。面对疑难,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向相关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原著等“求教”。前文所举“父执”“喧阗”,《现代汉语词典》中就有;“只眼”在《辞海》《辞源》中即可查到。至于“(一截还)东国”“粉骨碎身(浑不怕)”到底对错,最高裁判只能是原文。只要花点时间,认真查查有关的工具书和诗词集,此类误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善用工具书,是为学的重要途径,也是做好一名编辑必备的基本功,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养成严谨细致的良好作风
编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书稿的“检察官”,要忠实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既不放过一个错误,又不误改一个字词,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里边,工作作风至关重要。有了严肃谨慎的工作态度,即便有些问题一时弄不明白,暂时处理不了,也不至于贸然下笔,将错改错甚或将对改错。笔者有一个谬论:与其改错,不如不改。因为不改,至少还符合“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的“不知为不知”的古训。《论语》上说,孔子有四个不做: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妄加猜测,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凭主观印象判断。把《论语》上的这八个字用在稿件处理上,我看是非常恰当的。
特别注意对特殊情况的处理
书稿的性质各不相同,审稿中遇到的问题也千差万别,要善于总结经验,区别对待。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对以下几方面文字的处理,要慎之又慎:一是专名(人名、地名、职官名等)、专业术语、时间、数量等,在没有可靠根据以前,不可轻易改动;二是对于古籍、经典作品和直接引文等,应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原作的科学态度,一般不应直接更动(技术性改动除外,如加新式标点符号、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等)。
对第一种情形,毋庸赘言,第二种情形,这里想多啰唆几句。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其应用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我们认为错的东西,在历史上不一定是错的。而且,语言文字还具有极强的约定俗成性,只要社会认可了,都那么使用了,就无所谓错对了。
古籍、前人已成型的作品,反映了特定时代语言文字的应用情况,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拿现代汉语的标准、规范去衡量他们遣词用字的正误,用现代人的规范去作修改。举两个容易理解的例子,《论语》开篇的两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前句中的“说”是“悦”的通假字,后句中的“有”是“友”的通假字。说白了,“说”“有”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别字(类似的情况在古籍中很常见),但我们的祖先就这样写了两千年了,文本已经定型了,我们现在把它们直接改了,这怎么可以呢!又如,鲁迅作品中,有不少词的写法与我们今天不同,如“发见”(即“发现”),“刺戟”(即“刺激”),“雅片”(即“鸦片”),“那里”和“哪里”统用“那里”,助词“的”“地”区分不严,等等。切莫以为鲁迅写了错字,编辑把关不严,其实,这正是那个时代通行的写法、用法。不信,你可以看看鲁迅同时代人的作品。当然,不是说古籍和经典作品就没有文字差错,就绝对不能更正,只是态度要慎重,方法要科学。如果确实有差错,应当用校勘、注释的方式处理,切忌径改原文。
编辑要注意扬长避短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自己不懂的专业稿件,最好不要去“硬看”。现在有一种倾向很令人担忧,就是有些编辑什么稿件都敢接、都敢审;而且越是看不懂的稿件,审得越快(发现不了问题,自然省事)。如此,怎么能保证不发生误改呢?编辑人员一定要注意扬长避短,对稿件编辑加工怀敬畏之心,有所为有所不为。编辑加工过的稿件,应当尽可能送还作者审定确认,纠正可能存在的编辑失误。
行文至此,本当停笔,却忽然读到一篇文章,与本文谈的主题有点联系,不妨一叙。文章讲,著名诗人流沙河陪同台湾著名学者、诗人余光中先生游览成都武侯祠,看见张飞塑像前的解说牌上赫然写着“张飞字益德”。两位文人不禁大为愕然。流沙河先生想:“翼德”怎么变成了“益德”呢?此事若传出去,岂不让人耻笑我蜀中无人么?带着疑惑,流沙河回家赶紧查检《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见原文果真载着“张飞,字益德”。他这才如释重负,始知后出的小说《三国演义》上的“翼德”的写法不足为凭,解说牌上的写法准确无误。
读了这则故事,作为编辑,我首先想到,如果那解说牌上的文字出现在书稿上,我们会不会把“益德”改成“翼德”呢?(但愿这是杞人忧天!)其次,它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任何人所掌握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二是正确的东西要被认定是正确的,有时并不容易;三是有疑问,最好先作些功课,不可自以为是。对于克服本文谈的误改现象,这些启示难道不也是一剂“清醒散”吗?
本文选自
韩惠言《编学集》
甘肃民族出版社,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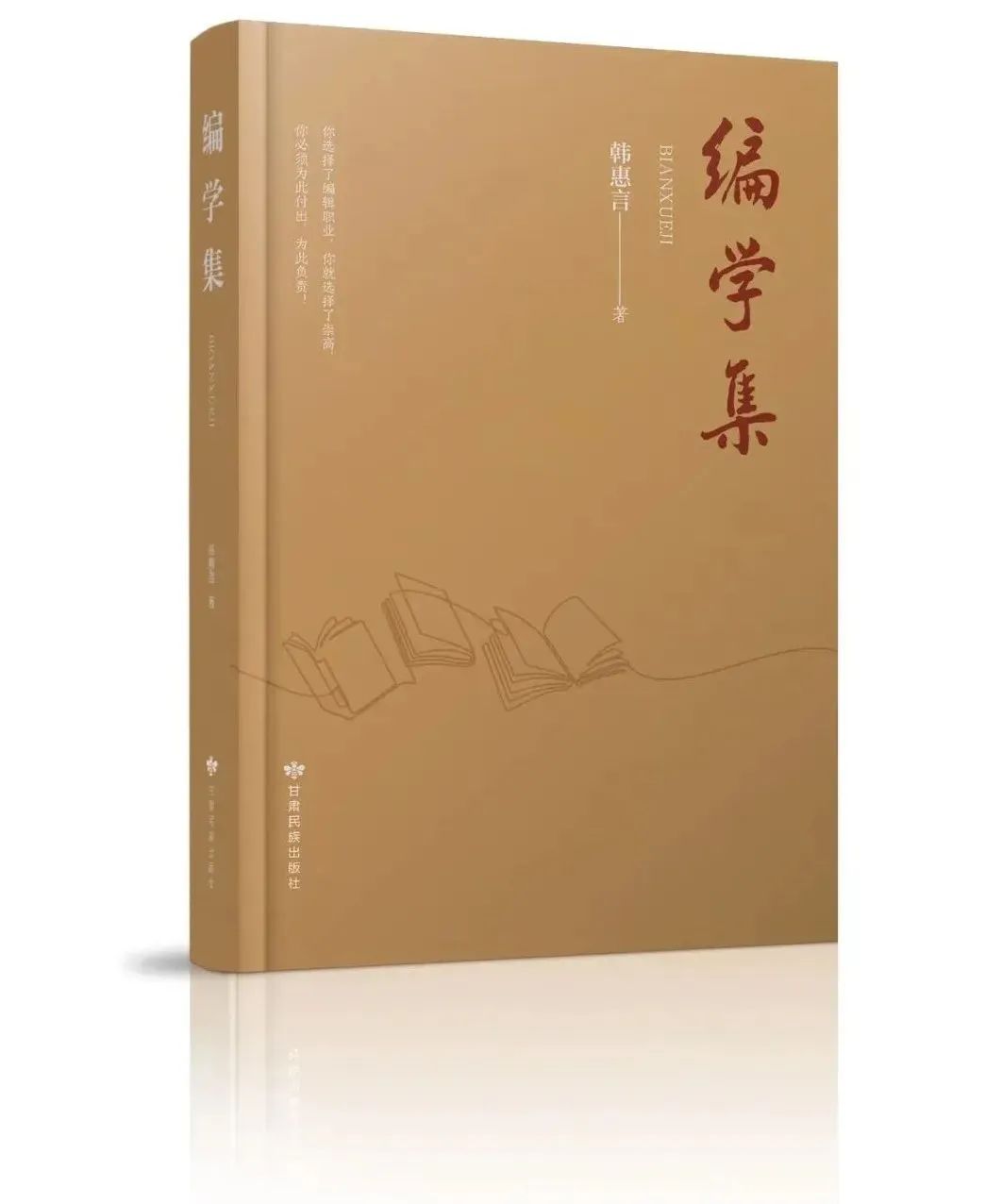
编学集
韩惠言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书号:978-7-5421-6608-1
定价:68.00
重磅预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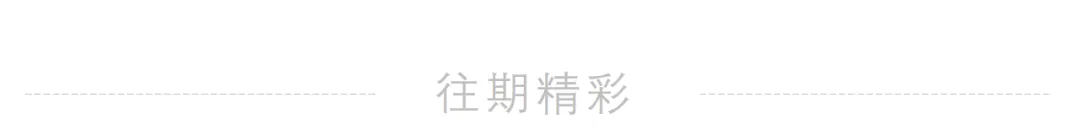
锐评出版业,看完瞬间破防!
从爆款到扑街:畅销书团队的跨界惨案
《哪吒2》等电影热映,相关图书狂销断货!
加入IP合伙人(站长加盟) | 全面包装你的品牌,搭建一个全自动交付的网赚资源独立站 | 晴天实测8个月运营已稳定月入3W+
限时特惠: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无限制下载点击查看会员权益
站长微信: qtw123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