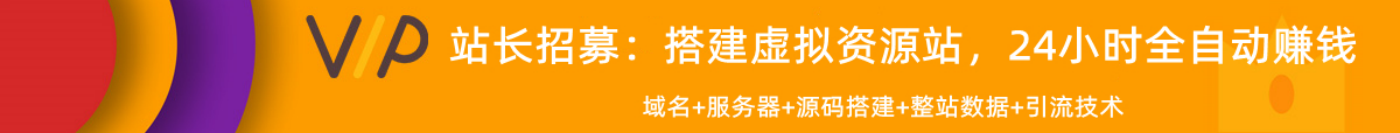裁判要旨
交通肇事后行为人虽然报警并积极救治伤员,但在协助调查时却隐瞒事实真相安排他人顶包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
关键词
交通肇事 逃逸 目的解释
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检察院诉称:被告人黄某鑫交通肇事致被害人徐某兴死亡。被告人黄某鑫虽在肇事后积极救助被害人,但仍指使随车驾驶员王某会顶包,不仅构成交通肇事罪,还具有肇事后逃逸的加重情节,提请依法判处。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3日5时许,被告人黄某鑫持“C1”型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且超载的豫G97×××(苏HM×××挂)重型半挂牵引车,沿S230线由南向北行驶至宜兴市周铁镇邾渎路口时,追尾撞到同向行驶的徐某兴驾驶的苏B36×××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致徐某兴受伤、车辆受损。后徐某兴因颅脑损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肇事后,被告人黄某鑫用手机报警并由他人陪同将徐某兴送至医院抢救,但指使随车驾驶员王某会顶包留在事故现场等候处理,且黄某鑫和王某会接受调查时均交代王某会为肇事时车辆驾驶员。
2015年8月19日,王某会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后其交代了为黄某鑫顶包的事实。同月29日,被告人黄某鑫经电话通知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如实供述了相关犯罪事实。
2015年9月3日,宜兴市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黄某鑫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和执勤的交通警察,听候处理;同时,应当如实向公安机关陈述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不得隐瞒交通事故真实情况。因此,保护事故现场、抢救伤者、报警并如实陈述事实经过,接受公安机关处理,是肇事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被告人黄某鑫在肇事后,因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履行法定义务,指使王某会作假证,主观上具有逃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为隐瞒肇事者真实身份而指使他人顶包的行为,逃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即便人当时未离开事故现场,也掩盖不了交通肇事后“逃跑”的本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其行为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情形。案发后,被告人黄某鑫接电话通知主动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应视为主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被告人黄某鑫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黄某鑫不服,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主要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是:黄某鑫指使他人顶包的目的是意图获取肇事车辆的保险理赔而非逃避刑事责任,客观上也积极救治被害人并未逃离现场,故不属于肇事后逃逸的情形,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遂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5)锡刑终字第0018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阅卷和提审所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上诉人黄某鑫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确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且系肇事后逃逸。上诉人黄某鑫案发后接电话通知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对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主要上诉理由和意见,二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黄某鑫不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规规定的法律义务,主观上具有逃避相应法律责任的意图,客观上实施了为隐瞒肇事者真实身份而指使他人顶包的行为从而逃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应当认定系交通肇事后逃逸;原审法院在量刑时根据上诉人黄某鑫的犯罪事实、结合其自首等量刑情节,并考虑到本案所造成的后果及其人身危险性,已对其予以从轻处罚,所处量刑并无不当。故相关上诉理由和意见不能成立。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评析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车辆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报警并救治伤员但安排他人顶包的行为是否构成肇事逃逸的法定刑升格的量刑情节。针对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该种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其理由是交通肇事逃逸的情节规定具有行为性,即《刑法》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规定是行为规定,而非行为目的规定,所以应当从行为性出发来解释肇事“逃逸”内涵,从而将不具有逃跑行为性的虽留在现场但安排他人顶包的行为排除在了交通肇事逃逸的范畴之外。[1]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其理由主要是从立法原意的角度出发,认为“逃逸”的内涵远大于逃跑,需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考量,而逃跑或者逃离现场只是“逃逸”的一种较为常见和明显的表现方式,但绝不能在两者之间画等号,错误认为没有逃离现场就不属于“逃逸”。笔者赞成后一种意见,理由又不局限于此,而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考虑:
一、法律条款字面文意与司法现实之间逻辑自洽的需要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从法条结构上看,本条规定了三个法定刑档次,其中第二个档次是: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就应当突破第一档次的限制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相关法律解释,“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2]是指事故造成的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结果,并非针对当事人的行为方式。所以本案中的安排他人顶包的行为只能考虑适用前半部分的“逃逸”的规定。
从词源学上讲,“逃逸”一词就是指逃跑,并且正常人的对“逃逸”的理解是人在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的行为,这也符合当前理论界和司法解释所主导的“逃避法律追究说”意见。[3]但是从法条的用词来讲,对“逃跑”一词在穷尽文意解释后,仍然无法将肇事者留在肇事现场安排他人“顶包”的行为纳入到“逃跑”的范围时,就说明对该条法律条文及个别用词存在进一步解释的空间。这也体现了法律解释方法对于处理法律适用中法律条文的不可周延性与案件事实不可预测性之矛盾的意义;交通肇事中的“逃逸”基于“逃避法律追究说”应该是指以任何作为和不作为的方式企图规避承当法律责任的行为。其立法原意上的外延显然比“逃跑”要更加广阔,因此将肇事后虽留下现场但安排他人顶包的行为界定为“逃逸”的类型之一或扩大解释进“逃跑”的范畴,这契合社会生活事实,具有生活经验上的合理性。
相对于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保险赔偿纠纷中肇事逃逸的认定来说,基于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特定性和不可转移性,一旦交通肇事者的行为进入到刑法规制的范畴,那么肇事者“逃逸”行为的认定自然要明确且不可回避。[4]那么基于刑事法律的严肃性,可以根据既往有关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将逃逸的构成要件解构成两个方面:一是主观方面,即具有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的意图。二是客观上具有逃跑、欺骗、编造隐瞒事实、安排他人顶包等多种表现形态的事实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其中主观方面最为主要,即只要具有了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观意图,其和任何形式印证这一主观意图的客观行为相结合都可以构成肇事逃逸。如此把握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可以解决狭窄字面文意与丰富法律事实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利于法律推演时罪名的法律用词在语义层面上实现立法原意与司法现实之间的逻辑自洽。
二、法律漏洞思维出发的填补性目的解释
刑法条文所规定的罪名具有高度的凝炼性,即争取用最简单的用词以表达最为直观、丰富、准确的含义。这使得罪名的外延很广,但内涵较为狭窄。但将刑法罪名下的具体法律条文和相应的罪名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前者所具有的内涵更为丰富,同时个别用词在外延上却表现的较为狭窄。具体到本案,从法律方法论角度考虑,对“逃逸”的理解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认定为积极的离开现场行为,然而,立法者基于法律事实的多样性,在立法时所赋予肇事后“逃逸”的含义显然远远广于“逃逸”这一直接字面定义。其实从法律本身的严谨性和法律语言的抽象性以及法律用词本身所涵盖的内容来讲,这算是一个隐藏的法律漏洞,[5]即该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的违反原计划的不圆满性。就本案而言,法律规定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与肇事“逃逸”之间就存在外延范围大小不能完全对应的漏洞,该漏洞所包含的范围就包括隐藏自己真正肇事人员身份从而逃避责任的形式。
法律适用的过程同样是一个法律解释的过程,这不仅包括将案件事实格式化为法律事实,还包括对作为大前提加以适用的法律条文的理解适用以及特定情况下对条文存在的法律漏洞的填补性解释。具体到本案来看,不具有驾驶特种车辆资格的行为人的驾驶行为造成交通事故,这一先前行为就产生了行为人因此应当留在现场积极救助的义务和如实向有关管理机关汇报并主动承担相关民事和刑事责任的义务。这些义务反映出《刑法》之肇事逃逸之规定所试图保护的法益,即事故被害人受到及时救助以免因耽搁致伤致死的权益和相关机关对事故进行顺利调查和处理以划分落实责任、平复纠纷的正常工作秩序。所以,对该条文内容的理解应当以此法益保护为出发点,从而得到符合法律规范目的的合理解释。即只要侵害了该法益的行为都可以涵盖相关的罪名和量刑情节中,该种逃逸行为最常见的是作为性质的,同时其不作为性质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从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出发,对“逃逸”和“逃跑”理解应当与交通肇事后逃避法律责任的多种表现形态的现实对应起来,即对“逃逸”做扩大解释,扩大解释的范围的限度应当逃避法律责任为限,即除开包含积极的、明显的逃离、撤离行为的逃跑行为之外,还包括积极或者消极的表现为各种形态的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从而填补这一法律漏洞。
三、案件判决针对现实情况的社会效果的需要
对一些事实问题的法律定性不应当完全局限于理论上的辩驳,因为定性的最终目的始终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司法实践,所以,在碰到类似问题时可以从现实社会需要角度作出更为合理的考量。近年来交通事故一直呈现高发趋势,因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在我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中高居榜首,形成了对公众的生命健康以及公共安全的巨大压力。鉴于此,《刑法修正案(八)》专门增加危险驾驶罪,将醉驾等尚未造成事故的行为纳入《刑法》惩罚的范畴,表明立法者针对驾驶机动车行为以及致伤致死结果在接受法律规制时从严适用的立法意思表示和意图,这也是为了实现遏制现今交通肇事致死的严峻形势的立法目的的必要举措。而肇事逃逸在现实中更是会对事故的进一步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会对他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更多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对所引发的矛盾纠纷的后续顺利调查处理增添巨大的麻烦和障碍,其法律惩罚的必要性尤为明显。
同时,肇事逃逸作为交通事故犯罪中独立的法定刑升格的考量情节,这不仅是要发挥《刑法》的惩戒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凸显《刑法》的警示、警戒意义,从而对尚未成立某种犯罪或法定刑升格情节但是又具有潜在可能的行为主体形成必要的威慑和预防。本案中的上诉人明知自己不具有驾驶特种车辆的资格,仍然强行逞能而为,在造成严重事故后安排他人顶包,表明行为人对自身行为企图免于适用《刑法》之交通肇事逃逸之规定的侥幸心理,为了避免类似侥幸心理酿成恶果,本案有必要对该条款予以严格适用以形成警示范例。
总之,解释法律不意味着抠法律的字眼,而是挖掘法律的意义和效果。本案上诉人基于人性中固有的趋利避害心理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选择安排他人顶包而自己积极救治伤员的做法,这样的行为表明行为人内心尚存良知与温情,并非是完全冷漠与危险性的主体存在,具有情理上的可理解性,可以在量刑时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考虑。然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对案件事实的定性除开极端个案之外是没有情理考量成分的,本案中的行为人的救助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立法者赋予法律条文本身的某种目的,但是其是在策划顶包试图隐藏自身责任的主客观状态下实施的,并非基于完整责任意识的行为,尚不足以符合《刑法》对行为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全面期待。同时,其行为毕竟侵犯了交通肇事逃逸之法定刑升格情节所保护的相关国家机关对交通事故的正常调查秩序的法益。从目的解释出发,以该法条的法益保护为导向,将“逃逸”扩大解释以对该条法律进行严格适用,这不仅符合立法原意,同时,也可以促进社会诚信意识的形成和社会公众责任意识的培养与强化,从而实现该类案件在今后司法处理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数据来源
人民法院案例选 2016年第9辑 总第103辑
审判人员
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王爱芳 潘明星 唐建平
二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徐海宏 蒋 璟 周 华 编写人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奇才 蒋 璟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王爱芳
加入IP合伙人(站长加盟) | 全面包装你的品牌,搭建一个全自动交付的网赚资源独立站 | 晴天实测8个月运营已稳定月入3W+
限时特惠: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无限制下载点击查看会员权益
站长微信: qtw123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