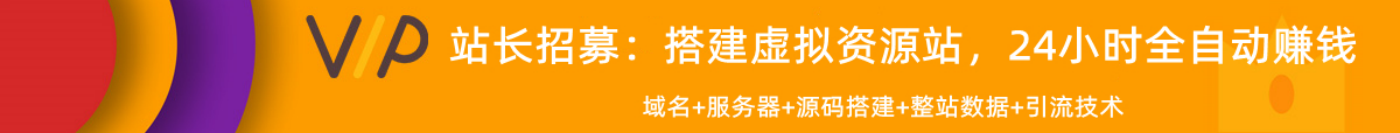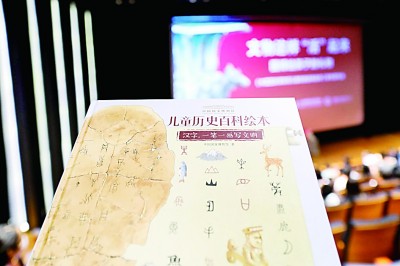摘要
古代商业市镇的起源与驿道交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与江南市镇兴起原因一样,广东历史上驿道交通的四条主要干线上,由于中央庞大的财政拨款及物资往来、官民不断增长的消费开支等经济活动,最终形成了繁盛的区域商业经济中心———镇。

早在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就指出,唐、五代以后的镇是一种区域性商业中心。加藤繁认为:“镇的名称,从齐、周、隋、唐,一直继续存在到五代,它的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唐、五代,节度使在他的管辖区域之内,设了很多的镇,置有镇使或镇将,并且使他们向人民征收粮饷器甲之费,地方行政的实权,离开了刺史、县令,而归于镇使、镇将。”“等到宋太祖、太宗夺去了节度使的权力,同时罢免了镇使、镇将,把他们的职权转给知县,所有的镇大概废止,只有在人口众多,商业繁盛的地方保存下来,设置镇官,使掌管烟火盗贼,并商税榷酤的事情。至于驻屯兵马,也尽量选择殷富繁华的地方。所以,从前虽有那样的倾向,但特别从此以后,镇完全是指小商业都市的意思。”
加藤繁还认为,宋以后大多数镇的崛起与驿道交通有密切关系。加藤繁说:“如果探索他们的起源,从名称来看,可以窥知,有的起源于农村,有的起源于馆驿,有的起源于以旅馆为中心的小部落,有的起源于桥畔渡头,人烟荟集的地方,而发展为镇,发展为市的那种地方,大概必须经过叫做草市,或者应当叫作草市的阶段。”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加藤繁的两个基本观点并没有大的歧议。国内也有学者循此思路对江南市镇兴起进行研究。但是,对驿道交通怎样促使镇产生的论述尚不充分,对广东历史上“路”与“镇”关系的研究更是空白。本文特补撰之。
一
宋代广东驿道交通与镇的兴起
宋代广东与中央及邻省驿道交通干线主要有四条。据《永乐大典·广州府》记载:“自凌江下浈水者,由韶州为北路;自始安下漓水者,由封州为西路;自循阳下龙川,自潮阳历海丰者,皆由惠州为东路;其自连州下湟水,则为西伯路。舟行陆走,咸至州而辐凑焉。”宋代粤籍名臣余靖还说,北路、西路及西伯路,“虽三道而下,真水者十七八焉”。即南雄经韶关,到广州是最主要的驿道。余靖没有谈及东路,其实,随着唐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不断开发,东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日渐上升。由广州至潮州,经漳泉,到福州,连接中国东南沿海主驿道的东路已成为仅次于北路的重要驿道干线。宋代东路分上下两路。上路走水路,从广州出发,溯东江至龙川,陆行80里,下梅江,转韩江,到潮州;下路以陆行为主,沿海岸线,经惠州、海陆丰、惠来、潮阳、到潮州。北宋时期,东路以上路为主。南宋绍兴29年,参知政事林宅主持了对下路的大规模修整,绍熙年间,转运使黄枪又兴建了多座庵驿,“自是潮惠之间,庵驿相望。”下路便取代上路地位成为东路主驿道。
宋代广东具有区域商业活动中心性质的镇已有相当数量。据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广东有镇共38个。它们分别是:广州有南海大通镇,番禺瑞石镇、平石镇、猎德镇、大水镇、石门镇、白田镇、扶胥镇,增城尼子镇;韶州有曲江氵蒙氵里镇,翁源玉壶镇;循州有龙川驿步镇;潮州有海阳角力州镇、黄冈镇、圃湾镇、里湾镇、净口镇,潮阳海口镇、黄冈镇;连山有阳山桐台镇、清泷镇;端州有高要三水镇,四会胥口镇;康州有端溪悦城镇、都城镇,泷水泷水镇;梅州有程乡李坑镇、梅口镇、双派镇、乐口镇、松源镇;南雄有保昌大宁镇;英
州有真阳的清溪镇、光口镇、回口镇、板步镇、浛光的浛光镇;化州有吴川渌零镇。
宋代广东的镇大多数分布在各主要驿道沿线。北路,自广州出发有白田镇、大通镇、石门镇、三水镇、胥口镇、回口镇、清溪镇、光口镇、濛浬镇、大宁镇;西路,自广州出发,至三水镇与北路同,以下有悦城镇、都城镇、泷水镇;东路,自广州出发有大水镇、猎德镇、瑞石镇、扶胥镇、尼子镇,转入上路有驿步镇、李坑镇、梅口镇、乐口镇、双派镇、松源镇、角力州镇、圃湾镇、里湾镇,下路有海口镇、黄冈镇,上下两路汇合于潮州,东出福建,仍有净口镇、黄冈镇;西伯路,自广州至光口镇,与北路同,以下有浛光镇、桐台镇、清泷镇。
宋代广东沿四大驿道线上分布的镇共34个,占宋代广东38镇总数的80%以上。可见,宋代广东镇的崛起与驿道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反,驿道不经的地区,如高州、雷州、新州、南恩州等就不见有镇存在的记录。北宋时期,东路以上路为主,所以,下路所经的惠州、海陆丰数百里也没有镇的出现。宋代广东的镇集中分布在广州、潮州、梅州、英州,这反映了上述地区是驿道交通繁忙的地区,也是宋代广东商业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
二
明清时期广东的驿道与镇的分布
明清时期,广东的驿道交通与宋代驿道交通有了较大的变化。第一,有些驿道的地位发生了变更。西伯路,秦汉至唐代,一直是广东通中原的重要驿道,也是广州至长安、洛阳的捷径,唐代韩愈《燕喜亭记》曾有扼要记述:“弘中自吏部郎贬秩而来,次其道途所经,自蓝田入商洛,涉浙湍,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足俞岭”。越五岭后,或下连州,或下乐昌。唐代张九龄凿大庾岭道后,广州至长安、洛阳,几乎全程均可利用水路,虽则时间稍长,但安全、舒适、运输量大等优点,使北路成为主驿道,西伯路地位迅速下降,明清时期,西伯路已不再是驿道了。第二,元明时期广东新辟了三条重要的驿道干线。第一条,是元初,塔刺海哈开辟广州至高、雷、琼、廉的新西驿道,笔者曾有专文。第二条,是元初,月的迷失开辟潮州,经福建汀州、邵武,江西建昌,抵江西行省省会隆兴(今南昌),笔者将另撰文详考。第三条,是在明朝万历初年明政府在平定了粤西地区的动乱之后,沿两广交界山区广东一侧,开辟了自南江口至高州的新驿道。至此,明清广东驿道已基本定型。它包括:自广州至韶州、转南雄大庾岭,抵北京的京广官马大路;自广州分水陆两路抵惠州,水路经龙川、梅州,抵潮州,陆路经海陆丰、潮阳、在潮州与水路合,然后东出漳泉,至福州接京闽官马大路,另自三河驿北上汀州、邵武、入江西南昌,又接京广官马大路;自广州溯西江,经端州,入广西梧州,接京桂官马大路;另自端州折南,沿恩平、阳江、抵高州,直至雷州、琼州及廉州、越南。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广东镇的数量又有了较大的增加。关于该时期镇的统计,虽则几个版本的《广东通志》均有记录,但笔者认为,取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清朝《嘉庆一统志》为底本,则更具全国性的衡量标准。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广东的镇共54个。它们分别是:广州府东莞福永镇,新安官富镇、缺口镇,三水三水镇,增城乌石镇,龙门上龙门镇,香山香山镇,新会沙村镇、从化流溪镇;连州阳山星子镇;肇庆府高要禄步镇、高明太平镇、四会南津镇、广宁扶溪镇、新兴立将镇、阳春古良镇、阳江海陵镇、恩平恩平镇;德庆州悦城镇、封川文德镇、开封古令镇;罗定州晋康镇、东安建水镇;韶州府曲江平圃镇、仁化扶溪镇、乳源武阳镇、翁源桂山镇;南雄府保昌平田镇、始兴黄塘镇;惠州府归善驯雉镇、博罗石湾镇、永安宽仁镇、龙川通衢镇、长乐清溪镇、兴宁水口镇、河源蓝口镇;潮州府海阳北关镇、潮阳吉安镇、兴安镇、揭阳北砦镇、程乡梅口镇、饶平黄冈镇、惠来神泉镇、大埔三河镇、澄海辟望镇、镇平蓝坊镇;高州茂名平山镇、信宜中道镇、化州梁家沙镇、吴川宁村镇、石城零绿镇;雷州府海康清道镇、遂溪椹川镇、徐闻东场镇。
清朝官修的《嘉庆一统志》共载清代广东的镇共39个,比《读史方舆纪要》所计少了15个。但是,清朝政府对修一统志极为重视,要求质量很高,所以,《嘉庆一统志》所载的广东各镇,应该是符合全国统一标准的。为免过于琐碎,转摘《一统志》所载各镇,均省去县名。
它们分别是:广州府佛山镇、扶胥镇、上龙门镇、香山镇、西南镇、良冈镇;韶州府三华镇、清溪镇;惠州府汕尾镇、回龙镇、利头镇、安民镇、平地镇;潮州府南澳镇、黄冈镇、三河镇、北关镇、千秋镇、丰顺镇;肇庆府青歧镇、高明镇;高州府硇洲镇、凌绿镇、中道镇、安村镇;雷州府清道镇;南雄府通济镇、浆田镇、圃田镇、上朔镇、沙水镇、黄塘镇、墨江镇;连州青龙镇、桐台镇;嘉应州梅口镇、清溪镇;罗定州罗苛镇、都城镇。综合二书所记,去除三水等9个重叠的镇,明清时期,广东境内实足93个镇。
我们比较北宋《元丰九域志》所载的镇和《读史方舆纪要》、《嘉庆一统志》所载的镇,不难看出有如下一些变化。第一:明清时期广东的镇比宋代的镇有了较大数额增长。北宋是38个,明清是93个,增长接近一倍半。第二:镇的分布也比较均衡。宋代,高州、雷州粤西南路诸州只有化州凌绿一镇,经过宋元时期的开发和元朝塔刺海哈自广州至高雷新驿道的开辟,明清时期高雷地区镇的数目达到10个。同样,惠州以东至潮州约400里的路程,宋代也没有镇,但随着南宋东路下路取代上路的地位,上路的镇减少了,但下路崛起了汕尾、回龙、利头、石湾等一批新兴的镇。第三:明清时期的镇大多数仍集中地分布在驿道沿线,或直接从驿站逐渐成为镇。当然,明清时期广东的镇也有些不在驿道交通线上,如海陵镇、硇洲镇、椹川镇、东场镇等。不过,我们这里尚不展开对它们形成条件的讨论,而集中研究为什么大多数的镇在驿道驿站上形成。
文章标题
给美好的春天寄封信
开辟了驿道,设置了驿站,就形成了一定消费规模,就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商业活动,这是商业性市镇兴起的主要原因。广东的情况也概莫能外。
早在宋代,广东一些重要的驿站就修得相当宏伟,甚至可以说是富丽堂皇。一般来说,驿站都叫驿,“而高大加饰焉,则易驿之名曰衙。”宋代潮州凤水驿就是其中之一。“潮居广府之极东,与闽岭比壤,凡游官于广者,闽士居十八九,自闽之广,必达于潮,故潮虽为岭海小郡,而假道者无虚日。”凤水驿内,“为榻著六案,与竹木匡床十有八席,以为荐藉各三十,器皿镬鼎悉备,使阍一人掌与窗与物之籍,而加钥焉。过客之车马及郡境,请预以告,授馆之礼当敬,从事无怠,虽然古君子所居一日,必葺其墙宇,去之日如始至。”元朝凤水驿改称三阳驿,规模更胜一筹。三阳驿内,“为堂前后有二,为廊前后有四,柱石坚固,垣墙周密,面阳辟户,气象轩豁,背山凿池,景仰幽胜,风月有时而自至,冬夏无适而不宜,汤沐饮食之需,供帐服用之具,件件精实[9]。”广东另一条重要驿道上南雄的驿站规模也很大。宋代南雄城内的驿馆竟有好几处。“州城内有八使行衙、寄梅驿,市南有凌江馆、近水楼,距城之东有沙水、怀德二驿。”其中,八使行衙“距郡治百余步,规模壮伟,屋宇高敞,他州莫及。”像这些规模庞大的驿站,从建造到维修,长年都配备了数量众多的工匠、花匠和服务人员,这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活动。
驿站的经常性开支也相当惊人。北宋初年,驿站的开支主要靠差役,当差及开支分摊在驿道沿线民户身上。过往官员一到,“则扶老携幼,具荐席,给薪水,朝夕执役,如公家之吏,不敢须臾离焉,俟其行乃去。”这种差役就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更严重的是大官未到,“尉之弓手,巡检之士兵,预以符来,需求百出,客或他之,则计薪,尽锱铢,取资直而去,民以为苦。”驿道沿线,“编氓远徙,不敢作舍道傍。”从南宋开始,广东驿道的开支转由财政支出。如南宋潮州知府陈圭就决定,济川、黄冈、桃山三驿站是重要驿站,岁费金钱一千四百余,“郡家独力为之。”又如南宋庆元间漕运使皇甫焕利用道观在南雄始兴设暖水道庵作驿站,“命道人一名在内掌守,每月支漕司钱米供瞻,专备汤饮,供往来行人,。[13]南宋时期,广东驿站的开支由临时征调过渡到有固定的财政支出,驿站人员由差役过渡到有固定的站户。
明清时期,广东所有的驿站都有庞大的财政拨款。如明朝广州府共有驿站19处,递运所2所,“每年通计派用银一万七千三百四十四两,派宽裕银九百两,二项共银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四两。”另征粮食“米二十二万四千四百六十石七斗四升。”嘉靖年间,广东驿站已不再征收实物,代之以当地米价折银征收,广州“一石该编派银八分一厘二毫八丝,”以八分计算,二十二万余石米,折银一万六千余两白银。征银和以银代粮二项合计,广州府驿站年支出三万四千两白银,平均每处驿站年财政拨款约一千七百两白银。广州的米价不算太贵,韶州府每石约折银一钱二分,惠州府每石约折银更达一钱五分多。[14]征收的数量也就更大。仅就正常的财政拨款来说,每个驿站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源,这就刺激了围绕着驿站形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商业活动市场。有些重要驿站,财政拨款则大大超过平均数。如“五羊、广州递运所各用银二千六百两,崧台用银二千两,凌江并车夫共用银二千四百两,芙蓉用银一千五百两。”这些耗资巨大的驿站更有利于市镇的率先形成。
清朝广东驿站的财政拨款也不少。据阮元《广东通志》载,清代广东全省共设驿站三十三处,“广东原额驿站银三万四千五百五十三两一钱二分,零存银二万七百三十一两八钱七分零,闰月加银一百五十六两有奇。”清代广东驿站平均年财政拨款约一千六百七十五两,与明代大致持平。
除财政拨款开支构成巨额消费外,过往官员及公差人员本身也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按规定,驿站必须向过往官员提供一定规格的招待。如明朝,“上司及府州县正官该银一钱二分,指挥州同县丞及首领官以下并书吏令史人等该银一钱。”[17]但事实上,有权势的官员往超出规定。“用银至四五钱有之,无关文而饣鬼送下程用银至七八钱有之。”[18]更有甚者,竟还索要戏班、妓女等。我们不用深追这些开支是由过往官员还是由地方官员来支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凡有大官要员经过,驿站就得张罗开来,就会形成一个大额的消费开支。像在广州至南雄,广州至潮州,广州至梧州这些连接全国主干线的驿道上,官员的往来络绎不绝,势必就大大刺激了重要驿站成长为市镇。下面就试举数则由驿站发展为镇的例子以证明。
饶平黄冈驿。“黄冈为闽广之交,山海之会”是潮州通往福州驿道上的重要驿站。黄冈设驿可追溯到北宋,《元丰九域志》就有记载,宋代开始形成镇,镇内“鱼盐之利,旁及郡邑,通货贸财,最为辐凑,”成为粤东巨镇。
大埔三河驿。唐宋以来,三河驿就是广州至潮州上路中的一个驿站。元朝广东道宣慰使月的迷失开辟潮州至江西隆兴新驿道,三河驿顿时成为两大驿道的交汇点,地位十分重要。据县志载:“三河,西通两粤,北达两京,盖岭东水陆之冲也。嘉靖初年,于镇北三十里建大埔县治以辖之,四境宁谧,生齿日繁,商舶辐凑,遂称雄镇,”[20]与饶平黄冈齐名。
三水西南驿。西南驿地处广州至梧州、广州至韶州两大驿道的交汇处,唐宋时期已是重要驿站。元代,西南并设水站、馆驿。宋代已成长为三水镇。明朝嘉靖五年立三水县,西南驿迁三水县城南门外西偏,围绕着西南驿又形成了西南镇。三水县城是政治中心,西南镇是经济商业中心,这一格局保持到近现代。西南镇,“南濒大江,商贾凑集,”[21]成为粤中重镇。据县志载,西南镇“米食多倚于西省”,“向有东顺商人射利,私设油榨,”[22]商业影响范围涉及东莞、顺德,乃至广西。
有些镇虽不是直接从驿站发展而来,但却与驿道交通有密切关系。
谈到明清时期广东的镇就势必要提及佛山。清前期,人们把它与朱仙、汉口、景德并称天下四大镇,又把它与北京、汉口、苏州并称为天下四大聚,成为闻名中外的工商业巨镇。然佛山镇的兴起正是驿道交通线路改变的直接产物。直至明朝以前,中原经北江到广州的主驿道均不经佛山,北江顺流到清远后,先是从石角入白泥水,经石门抵广州,故今广州市北郊石门宋代便是名镇,后是经芦苞涌,入官窑,抵广州。到明代才开始经佛山涌入广州的。明朝天启年间徽商程春宇《士商类要》对驿程的改变有准确记载:“清远县,安远驿,共九十里至迥岐驿,共六十里胥江驿,此处有河二道。水大,由芦巴水口至官窑驿止七十里;水小,一站至西南驿。”清代京广主驿便大多经由佛山了。清朝康熙《南海县志》载:“考北江抵省故道,初由胥江、芦苞、趋石门,尚未与郁水合。迨芦苞淤塞,下由西南潭趋石门,始与郁水合流;后西南潭口再于淤,今由小塘、紫洞入王借冈、沙口、趋佛山、神安,南往三山入海。”[24]驿道交通的演变,使石门镇衰落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的兴起。清朝《嘉关一统志》首列佛山镇。”“佛山镇,在南海西南四十里,当入府孔道,为县大镇。”笔者还注意到,成书于康熙年间的《读史方舆纪要》并没有列出佛山镇,这不是顾祖禹疏忽,而是佛山尚未发展到镇的规模。佛山镇的鼎盛时期应在清朝康熙以后。
与佛山镇地理位置相类似的还有扶胥镇,因处于广州至潮州、福州东驿道上,也是广州海外贸易海上丝路的始发点,西江、东江、北江三江之水汇合点,故扶胥镇又名“三江口”。扶胥镇的商业活动一直非常繁盛,历代过往官员更留下无数墨迹,成为广州近郊的名镇。
由于驿道驿站是国家主要物资运输、官员往来、信息传递的重要命脉,历代统治者均大力加强对驿道沿线的治安建设,以确保驿道交通的畅通,这也对驿道驿站发展为镇起促进作用。如明朝政府就规定:“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驿站往往就是“天下要冲去处”,明代黄冈、三河、西南、禄步、悦城、清溪等巡司便都设有弓兵各五十人。为保治安,明代广东各镇还纷纷筑修起城墙。如明嘉靖年间修黄冈镇城墙“内外皆秋瓦以石,周围一千二百余丈。”商业活动就可以在镇内正常进行。
镇的产生与商人利用驿道系统也有关系。古代中国驿道驿站设置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信息传递及过往官员公差的安全,但也常被商业所利用。开始应该是官商利用。如宋初赵匡胤为从广东运输香料,下令规划重修大庾岭驿道。最盛时,“岭南输香药以邮,置卒万人,分铺二百,负担抵京师。”真宗咸平五年,改以水运为主,“止役卒八百,大省转运之费。”可见,驿道的官商运输功能是十分明显的。明代以后,民商利用官驿系统更是普遍的事情。明万历年间,徽商黄汴修《一统路程图记》,详记明朝疆城内各驿道驿站;所记广东各驿站里程大致正确。关于编书目的,黄汴说:“宦轺之所巡,商泊之所趋,访屐之所涉,庶此编为旌导也。”[30]明万历年间,两广总督凌云翼新辟自西江南江口,经罗定、到高雷地区驿道,他在上朝廷的奏章中也强调,修驿有利于把高雷地区过剩的粮食运回广州和梧州。凌云翼说:“以南北孔路直贯泷水之中,不惟血脉弗滞,而货财往来元气更易充实。”[31]其商业目的是非常明显的。民间商人及旅客普遍利用官驿系统,更大大促进了驿道上的商业活动及镇的最终形成。
明清时期,广东对镇的性质是有明确界定的。“民人屯聚之所为村;商贾贸易之所为市;远商兴贩之所为集;车舆辐辏为水陆要冲,而或设官将以禁防焉,或设关口以征税焉,为镇;次于镇而无官司者为埠”。而古代广东大多数主要的镇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先是开辟了驿道和设置了驿站,然后是围绕着驿道系统开始了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商业活动达到一定规模的就有了税收的必要和管理衙门,派驻了军队,甚至筑起了城墙,于是镇也就产生了,有些镇甚至还逐渐由商业活动中心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发展,成为新生县一级政权的所在地,由此带动起驿道沿线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恐怕就是古代广东“路通财通”的辨证关系吧!

chūn
春
nuǎn
暖
huā
花
kāi
开
原文载于1999年第1期广东教育学院学报,限于篇幅,注释不载。

加入IP合伙人(站长加盟) | 全面包装你的品牌,搭建一个全自动交付的网赚资源独立站 | 晴天实测8个月运营已稳定月入3W+
限时特惠: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无限制下载点击查看会员权益
站长微信: qtw123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