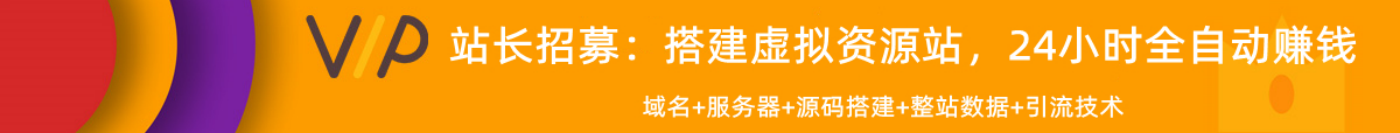[摘要]战国秦汉时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地名资料都存在讹字、异文等情况。传世文献中地名讹字的原因多是形近致讹,出现讹误的时代各不相同,少数讹误在古文字阶段即已发生,多数产生于隶楷阶段。出土文献可以为校订传世文献地名讹字提供直接证据或者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把通假、省形、形近偏旁混用与真正的讹字混为一谈,同时要注意出土文献也会存在抄写错误。校订地名讹字时,字形因素之外,还需要注意不同时期的用字习惯、误倒、误拆误分、脱字以及地理沿革等各种情况。
[关键词]战国秦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地名讹字
战国秦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资料是研究同时期出土文献地名的基础,但传世文献中的地名时有文字讹误、异文等情况,这一问题可借助出土文献来加以校订。学者在利用出土文献校订战国秦汉古书中的地名讹误方面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仍有一些地名讹字有待纠正,已有研究中的某些疏误还未能厘清。本文拟对战国秦汉传世文献的地名讹字资料举例说明并讨论相关问题。
一
《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时有讹误,南北朝以来的学者对此多有纠正。比如,《战国策·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章、《韩非子·十过》中的“又使人之赵请蔡、皋狼之地”,鲍彪、吴师道已指出“蔡”为“蔺”字之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集解》引徐广日:“‘郑’当为‘鄚”’;《汉书·王子侯表》临朐侯条下注“东海”,全祖望、梁玉绳已指出实为“东莱”之误。晚清以来的学者还卓有成效地使用出土资料纠正传世文献地名的讹误,比如,吴式芬、陈介祺据汉代“扦关尉印”封泥证明《续汉书·郡国志》巴郡鱼复县“扞关”确为“扞关”之误;劳榦依据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怀疑《盐铁论·复古》“扇水都尉”的“扇水”或为“肩水”之误;林沄据西汉封泥与铜印文字考证《汉志》玄菟郡“夫租”应作“夭租”等。
综观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讹字可知,地名讹误存在不同的类型与致误原因,相当数量的地名讹字是形体相近致误,此外还有误倒、误拆、脱字等情况。下面分别说明。
形近致讹是地名讹字的主要原因,其中既有单个字的讹误,也有偏旁形近讹误。如《汉志》中琅邪郡“雩叚”(一作“雩段”)即《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城阳顷王子侯国“雩殷”,《汉书·王子侯表》作“虖葭”,梁玉绳、王先谦已指出“殷”“段”均为“叚”之形近误字;五原郡“南興”,齐召南改为“南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458号简文正作“南舆”;武都郡“循成道”,王念孙已指出为“脩成”之误,已为敦煌汉简“脩成”资料证实;西河郡“千章”,据西汉铜壶刻铭应作“干章”,东海郡“于乡”当为“干乡”、“海曲”应为“海西”,已被尹湾汉墓简牍证实;定襄郡“定陶”县,汪本作“安陶”,西汉封泥文字证实当以“安陶”为是;雁门郡“阴馆”县“莽曰富代”,《水经注·漯水注》作“富臧”,南阳郡“穰”县“莽日农穰”,《水经注·淯水注》有“丰穰”,新莽封泥(《马编》524号、104号)证明“富臧”“丰穰”为是;《汉志》“泗水郡”,《史记》《汉书》刘邦的本传中均作“泗川”,《续汉书·郡国志》亦载沛国本“泗川郡”,秦简资料证实以“泗川”为是。此外,《史记·韩世家》《六国年表》中的韩景侯元年“伐郑,取雍丘”,“雍丘”为“雍氏”之误。
《史记·礼书》“(然而兵殆于)垂涉”,王念孙已指出为“垂沙”之误,《汉书·地理志》魏郡“沙”县,王念孙已指出为“涉”之误。这是涉、沙二字互讹。《汉志》河南郡“平”县“莽曰治平”,汝南郡“
”县“莽曰闰治”,从新莽玺印“洽平马丞印”“润洽县徒丞”来看,治平、闰治的“治”实为“洽”字之误;《汉志》梁国“下邑”县“莽日下洽”,“洽”汪本作“治”(《水经注》亦作“下治”)。这是“治”“洽”二字互讹。
偏旁形近致讹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城阳顷王子封邑“涓”,《索隐》:“《汉表》作‘淯’”。王念孙认为“俗书‘涓’字作治
,与‘淯’相似而误”。马孟龙认为《水经注·泗水注》载南梁水亦称涓水,城阳国的涓地当在此处。汉代文字中的“
”旁与“育”形相近似,是“涓”讹为“淯”的主因。《汉志》西河郡“徒经”为“徒淫”之误,其实早在战国楚简中已经出现了“
”旁与“
”形体混同的情况,比如郭店简《缁衣》第6号简、《唐虞之道》第12号简“淫”写作“泾”等。
有的地名讹字最初只是偏旁的形近混用。比如“
”与“易”、“
”与“虎”、“
”与“麦”作为偏旁时的混同比较典型的例子可举出《汉志》汉中郡钖县,《续汉书·郡国志》益州汉中郡作“锡”,战国秦兵器王四年相邦张仪戈(《铭像》17263)刻有置用地“铴”、湖北郧县出土有汉代“铴仓”封泥,而西汉初张家山《二年律令·秩律》第454号简文“铴”县、新莽封泥“铴县马丞印”中均写作“钖”,反映了秦汉时代“
”“易”偏旁混同的情况。“阴”与“陶”在汉代文字中有形近混同的情况。《战国策·齐策四》“苏秦自燕之齐章”:“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吴师道云“阴即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亦作“陶”;《穰侯列传》“复益封陶”,《集解》引徐广日“一作‘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15章“有为阴启两几,尽故宋”,“陶”字即写作“阴”形;张家山汉简《秩律》第459号简“馆阴”之“阴”实用作“陶”字;《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成陶”,《集解》引徐广日“一作‘阴’”,《索隐》:“《汉表》作‘成阴’,《汉志》阙”。这些反映的都是“阴”与“陶”形近相混的情况。
有些地名讹误属于文字脱漏、误倒所致。《史记·秦本纪》载:“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六国年表》和《魏世家》都说此年秦拔魏四城,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根据《编年记》秦昭王三十三年“攻蔡、中阳”,认为《秦本纪》的“蔡阳”系“蔡、中阳”之误,即脱漏了“中”字;《汉志》玄菟郡“上殷台”县“莽曰下殷”,根据王莽改名的规律,此处“下殷”后面脱漏了“台”字。《汉志》临淮郡“盱眙”县“莽曰武匡”,《水经注·淮水注》作“匡武”,新莽封泥文字确认“武匡”应为“匡武”之误倒。
有的地名讹误时误分一地为二,比如《汉志》北地郡的“方渠”“除道”,据秦封泥“方渠除丞”可知是误分一县为两县(道);有的是将一字误拆为两个字,比如《汉书·王子侯表》城阳王子“辟土”侯,从汉代封泥“壁乡”来看,则是误拆“壁”为“辟土”二字心。
有些地名最初是由隶入篆导致异体,并最终演变为讹字。《汉志》东郡、《续汉志》东平国“须昌”县,《洛泉轩集古玺印选萃》041号西汉官印文作“须昌”,《征存》962号东汉官印文作“
昌”,因隶书中的“
”“水”偏旁形近,故篆文将“须”写成了“
”;《汉志》零陵郡有“泉陵”县,《汉书·王子侯表》有“众陵节侯贤”。从《征存》291号“泉陵令印”来看,印文“泉”字与《曹全碑》“泉”字相近,应当是由这种写法的隶书形体入篆而被误认作“众”。盯。《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
川懿王子始昌的封邑“临原”,《汉表》作“临众”,情况类似。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组资料都属于东汉时期,可见汉代隶书对篆文印章字形上的影响,这些异写在当时虽不会引起误认,但客观上造成了后世的地名讹字。
二
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部分地名写法不一,并不都是文字讹误。清代学者梁玉绳、王念孙等已注意及此,将“隆虑”与“隆卢”、“众利”与“终利”、“枸”与“朐”视为“古通”“字通”“借字”的关系,甚有见地。此外,校订地名讹字时还有一些倾向需要修正,包括忽略不同时代的用字习惯、误定为讹字、不能及时吸收已有校订成果、误用出土文字资料等。
《史记》《汉书》中的“荥阳”地名,清代以来的学者根据汉代封泥、汉唐碑刻资料认为应是“荧阳”之误。吴振武认为:“从这些古书的成书年代看,书中的‘荥阳’之‘荥’写作‘荧’是完全可能的”,但从“时代更早的战国古印资料来看,‘荥阳’之‘荥’原本就作‘荥’,则是毋容怀疑的”。施谢捷认为:“‘荥阳’之得名与‘荥泽’有关,‘荥’本来应该作从水的‘荥’,秦汉以后或作从火的‘荧’,则属于同音借字。至于后世文献中作‘荥’或‘荧’,只是反映不同时代或不同书手的不同用字习惯,并不存在孰是孰非。”吴、施的说法无疑更为允当。今按,从“
阳”(《古陶文汇编》6•107、108、《王氏集古印谱》,韩)、“萦阳上官皿”(《铭像》22•1249,韩)、“荧阳矛”、“荧市”(《陶文图录》6•408•4)、“荧阳丞印”(《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74,秦)来看,战国时期韩国同时存在从“水”、从“糸”两种写法,战国秦及秦代文字则从“火”形,汉代的“荥(阳)”除了从“水”“火”两种异体,汉简里还有从“目”的写法。可见地名“荥阳”在战国秦汉每个时期都有两种以上的写法。从用字习惯上说,不能机械地认为《史记》《汉书》中的“荥阳”是“荧阳”之误。
《汉志》颍川郡“纶氏”,《续汉志》作“轮氏”(《续汉书》其他篇中或作“轮氏”,或作“纶氏”)。马孟龙结合北大藏秦简、东汉碑文与刑徒墓砖文等资料认为,“由秦至东汉该县都书写为‘轮氏’,今本《汉志》‘纶氏’并非汉代通用的写法,这对于校订《汉志》文字讹误,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今按,秦代至东汉时期“纶氏”地名确实以作“轮氏”者最为常见,该地名在战国时期则有“纶氏”(《水经注》引《竹书纪年》)、“
氏”(《汉瓦砚斋古印丛》、《古钱大辞典》252,韩)、“仑氏”(《集成》11322戈)或“仑”(《古玺汇编》0341)等不同用字,这些均属于文字通假关系。虽然目前暂不知两汉官印、封泥中“纶氏”是否写做“轮氏”,似不宜视《汉志》“纶氏”为讹字。类似的情况还有《汉志》西河郡“圜阴”“圜阳”之“圜”,战国三晋文字中写做“言、
”(《货系》1376桥形布币、3994直刀币、《铭像》16818戈),秦文字里作“
”(《十钟山房印举》2·55),两汉文字里多作“圜”。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一四·壹号简将“伊阙”之“阙”写作从门、从旅(以下用A代替),整理者、黄盛璋认为A是“阙”的讹字,裘锡圭疑六国文字与汉印中的“阏”为A的讹字、A为“闾”之异体。郭永秉认为:“从秦汉文字资料中‘A’字的用法看,不少‘A’字是读影母月元部音,所以此字大概就是《说文》训‘遮拥也’的‘阏’字(即古书“拥阏”之“阏”,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本字或异体。……与古音为溪母月部的‘伊阙’之‘阙’十分接近,故可通假。”再比如,《战国策·齐策五》“苏代说齐闵王”章:“赵得是籍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鲍彪改“棘沟”为“棘蒲”。《汉书》棘蒲刚侯陈武,杨树达根据《封泥考略》卷6“棘满丞印”认为“棘蒲”为“棘满”之误。赵平安认为,“棘蒲历代古书用例较多,棘满目前仅此一见”、“满是蒲的讹字可能性较大”并认为“实用印上有讹字,是比较罕见的现象”。今按,实用印中出现讹字,目前尚未见到确切的例子,古书中的“棘蒲”极有可能就是印文“棘满”的异写。
《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
川懿王子的封邑“平酌”,《索隐》:“《汉表》作‘平的’”,《汉志》北海郡有“平的”侯国、《汉书·王子侯表》有“平的戴侯强”,罗福颐等依据“平的国丞”印(《两汉官印汇考》1069号)认为“的”“酌”俱为误字。《汉志》东郡茬平县,《续汉书·郡国志》作“茌平”,陈直据《景君碑》“济北茬平”定后者为讹字,而出土文献也写作“茬平”(张家山汉简《秩律》460号简、《肩水金关汉简(五)》C:425、《新出封泥汇编》2949),泰山郡“茬”县,宋祁认为应作“茌”,王先谦及之后的学者多认为“茌”属讹字,周寿昌认为“茬”为“荏”之俗省。实际上这两组地名均属于通假关系(《续汉书·郡国志》济北国、泰山郡作“荏平”“荏”,“荏”才是真正的讹字)。
学界在探究地名致误原因时,于字形因素之外或试图从用法角度加以解释。比如,《汉志》辽西郡“宾从”县,王先谦《汉书补注》已引据《续汉志》《晋书》改为“宾徒”,罗福颐又据“宾徒丞印”加以证实;新莽官印已证实《汉志》河南郡“平”县“莽曰治平”为“洽平”之讹,或认为“宾徒讹成宾从可能和它们用法相通有关”,“洽平和治平都成词,都见于文献。……洽平写作治平,不仅与形有关,也与意义有关”。实际上,字形讹误与它们能否成词、讲得通,二者有着质的区别。
出土文献中也存在书写讹误的情况,其中地名被写误的并不少见。比如,张家山汉简《秩律》第451号的地名“漆”误写为“沫”、“
”误写作“楬”,第454号简“灌泽”为“
泽”之误书,第456号简“醴陵”为“醴阳”之误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15章误书“单父”之“父”为“尤”,第16章误书“茅”为“茀”、“文台”误书为“支台”等。这说明对出土材料不能有迷信的态度,同时也提醒学界不能反以传世文献中的误字为正。这里试以张家山汉简“扜关”为例,晚清时期的学者就已据封泥文字指出“扞”为误字,张家山汉简整理者不仅没注意西汉时期的封泥文字资料,也没有及时吸收张家山汉简地名研究的意见,一直以简文“扜关”之“扜”为“扞”误字。从西汉时期的出土文字资料以及《玉海》卷24“楚扜关”条所引《楚世家》《战国策》《盐铁论》来看,《战国策》《楚世家》“扞关”之“扞”都是“扜”的误字。
“扞关”还见于《战国策·赵策一》:“今燕尽韩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钜鹿之界三百里,距于扞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赵世家》则说“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距麋关,北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从方足小布“干关”的面文来看,《赵策一》的“扞关”应无误,而《赵世家》的“挺关”属于误字,至于“麋关”与“干(扞)关”的关系则待考。
校订古书中的地名讹字,有时还需要考虑地理沿革等因素。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这句话,武英殿本作“秦取我西都及中阳”,南本、枫本等则作“秦取我西都及云阳”。相应地,《六国年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栏记载此事作“取赵中都、西阳”,或作“取赵中都、西阳、安邑”。梁玉绳曰:“‘中都、西阳’乃‘西都、中阳’之误,说在《秦纪》。而‘安邑’是魏非赵地也,《秦纪》《赵世家》皆无之,此与《赵表》‘安邑’二字并衍文(自注:《秦纪》《正义》引《赵表》作‘中都、安阳’,亦非)。”张文虎云:“各本‘中’‘西’互误,《考证》据注及《表》改。”单从版本的角度难以决断“中都、西阳”“西都、中阳”何者有误。从张家山汉简《秩律》第452号简所载“西都、中阳”排在上郡属县“徒淫”之后、“广衍、高望”之前以及陕西米脂出土的东汉墓葬画像石刻铭等资料来看,西汉以来的中阳县位于今陕西境内;西都见于《汉志》西河郡,“莽曰五原亭”,由此可知该地一定在今陕北地区,临近西汉五原郡界。从已经公布的金属铸币资料来看,赵国铸造有“中阳、西都”面文的尖足布币、“中都”方足小布(《货系》1034、1042、1549),尚未发现“西阳”面文的三晋货币(传世文献中也见不到三晋地区有“西阳”地名)。既然中阳、西都均位于今陕西而非山西境内,而《赵世家》的记载又表明,赵国涉足今陕北地区不得早于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那么武灵王十年时秦国夺取的赵地就不可能有“中阳”,《赵世家》武灵王十年时的“中阳”应是“西阳”之误。由此可知,当以金陵本“秦取我中都及西阳”为是。
学界也偶有误引传世文献、误用出土材料的情况。比如,罗福颐认为《汉志》庐江郡无“睆”而只有“晥”县,“晥”乃“睆”之讹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又由“晥”讹为“皖”,实际上《汉志》庐江郡“睆”县被罗文误引作“晥”,《封泥考略》五·八收录的“睆长之印”恰恰证明《汉志》与出土文献写法一致。陈直据新莽官印、封泥指出《汉志》乐浪郡“邪头昧”县之“昧”应为“眯”之误,颜注引孟康日“昧音妹”,可知孟康所见本已讹。周振鹤提出“颇疑邪头昧之昧有貊音,邪头昧即邪头貊,为涉貊之一支,故以之为县名。陈直云《书道》卷3有‘邪头昧宰印’封泥,盖传写之误。究其实,恐非传写之误,以记貊之音,而或为昧,或为眛耳。”舯陈伟武认为“眯”“眛”二字既可能是形讹,也可能是音假关系。今按,周文转引陈直所说新莽封泥文字有误,应为“邪头眯宰印”;无论是“眜”“眛”还是“昧”,从音读上都无法解释清楚与“眯”的关系,只能是形近讹误。再如,《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城阳顷王子侯国“
”,《集解》引徐广日:“一作‘报’”,《索隐》引师古日:“即‘狐’字”。钱穆认为:“‘
’与‘报’皆‘执’之讹。《说文》《玉篇》有‘执’无‘
’。河东
,乃‘瓠’讹。”一狮马孟龙认为:“山东临沂市出土战国戈见有‘
’字,知西汉城阳国确有‘
’。
侯国初封当别属东海或琅邪,后徙封北海郡。”临沂出土铜戈(《铭像》16298)铭文实为“
(郜)”而非“
”字,郜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与西汉城阳国无涉),不能用来判断《史记》地名“
”“报”何者为误字。
有的古书地名是否为讹字,学界争议较大。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学界一直对“鄢郢”所在地争议颇多。黄盛璋推测其为“陈郢”的讹误、“引兵而西”之“西”为“东”之讹’,辛德勇推测“鄢郢”为“荆郢”之讹,实际上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李信攻破的楚国鄢郢该如何理解,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意见。
END
加入IP合伙人(站长加盟) | 全面包装你的品牌,搭建一个全自动交付的网赚资源独立站 | 晴天实测8个月运营已稳定月入3W+
限时特惠: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无限制下载点击查看会员权益
站长微信: qtw123cn